“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8月16日上午10时许,在弘一大师优美感伤的《长亭送别》歌声中,四祖寺第十届禅文化夏令营在双峰讲堂落下帷幕。突然,一位男营员向现场300多位沉浸在离情别绪中的“同修”提议:“让我们把掌声献给崇谛法师,感恩他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营员们不约而同地起立,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讲台旁一位颀长俊朗的年轻法师,热烈的掌声瞬间潮水般淹没了讲堂的每一个角落,营员们的心融化在一片感动中。
一直在夏令营活动中指挥若定的崇谛法师,却在掌声中窘迫起来,他红着脸打岔说:“不要耽误时间,大家赶快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午餐后寺院安排了大巴送大家走!”
在营员们眼里,崇谛法师几乎是一个神奇的偶像:年纪轻轻却无比干练,才华横溢而十分低调。极其繁忙却从容不迫。他每天都起得最早,睡得最迟。从凌晨5时到晚上10时,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无比辛劳却总是笑容灿烂;从大型活动中妙语如珠的主持人,到远程行脚、汗湿僧袍的领路者,从卖力的搬运工到佛教歌曲的领唱人,他频繁地在截然不同的角色中自由转换,毫无障碍。
可以说,7天的夏令营,营员们除了从晨钟暮鼓、诵经打坐、大师讲座、户外行脚、普茶传灯等精彩纷呈的活动中,体验似乎无处不在却又无形无相的生活禅,最生动直观的“活教材”,莫过于始终和大家如影随形的崇谛法师。
虽然年纪轻,崇谛法师却绝对已经是一本十分厚重而又灵动的“大部头”书,而向来低调的他,很少向大家“展示”。这次,经不住笔者“狗仔队”式的“穷追猛打”和“反复纠缠”,崇谛法师充满传奇色彩的学佛经历,终于在闭营仪式后的采访中浮出水面。
与佛法间一场轰轰烈烈的“早恋”
令笔者无比惊奇的是,早在童年时代,崇谛法师就已经有缘亲近了佛教。这个生于关东大地、天资聪颖的少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热烈地爱上佛法,并与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早恋”。
从五、六岁记事开始,一个比天还大的问题就反复撞击他的心房:人为什么会死?死了以后去向哪里?法师幼小的心中充满恐惧,同时也悄然埋下了探究的种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同学家中看到的两本书让他眼前一亮:《礼敬佛陀》、《觉海慈航》。如饥似渴地读完,犹如久旱逢甘霖,心里说不出的舒坦。为了能够进一步地了解佛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给福建莆田广化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要请到一些法宝的愿望,不久真的如愿以偿。听说离家30公里地的一个寺院有位很有修行的老尼师,初一暑假,他瞒着家人,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寺院,向尼师求法问道。
从初二开始,满腔慈悲心的少年实在忍受不了吃众生肉,宣布与家人“分灶吃饭”:自己一个人吃素。
连形象上也越来越“佛化”了:脚下一双僧鞋,手里一串佛珠,嘴里念念弥陀。受三皈五戒后,得到一件向往已久的黑色海青,像同龄人得到一件国际顶级名牌时装一样,一回家就在镜子前试穿,兴奋不已。
然而,在数千年的文化自信被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击碎后,在构筑中国人文化根基的儒释道文化传统被历次的浩劫反复“革命”后,佛教的地位一落千丈,佛教徒成为人们眼中难以理喻的“边缘人群”,“高调信佛”的他在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时代成了一个十足的异类和“怪物”。
于是,一场又一场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父母担心学佛会影响儿子的前途,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参加了什么邪教组织。倔强而又雄辩的他拿着宪法和父母辩论:“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文斗”失败,武斗上演,年少无畏的法师因之而不断遭受皮肉之苦,每每从寺院抓回家后,就免不了一顿打。
讲完这段令人感慨的学佛经历,崇谛法师对笔者说出了自己的反思,“现在想来,我这种十分张扬的学佛方式其实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不顾周边环境、不管家人感受,不仅让他们痛苦担心,而且还引发对佛教的反感甚至诽谤。真正的学佛信佛不应该执着于形式和外相,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展示佛法的正能量。”

遇到净慧长老,开始了新的生命里程
“后来我越来越清楚,我就是为当和尚而生的”,崇谛法师回忆。从初中开始,少年的他就坚定了出家的想法。初三的一天,父亲跟他有一场关于人生前途的对话。父亲问他,“你想出家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父亲说,“那就不能结婚,不能过普通人的生活,你知道吗?”“我知道。”年少的他内心十分坚定。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青春期的法师越来越成熟理性,他懂得了父母恩重难报的道理,打算在不放弃学佛的同时,集中精力把学业搞好。高考结束后,他远离家乡,来到武汉求学。他将出家的时间表定在考研并工作两年后,这样可以让父母好受一些。
没想到,机缘突如其来地降临了。
“我跟老和尚的缘分是不可思议的”,崇谛法师说。早在高一时,因为内心的苦恼,他曾给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刊《法音》杂志写信,倾诉自己因为信佛与家庭和学业的冲突,表示自己内心想出家但又怕家人难以承受。没想到,很快收到主编净慧法师的回信,信里告诉他,要处理好信佛与学业的关系,首先要把学业搞好,不要急于想出家。
“那时候,我压根没想到这个人会成为重新塑造我生命的人。”
在武汉读大学期间,除了搞好学业,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寺院和书店,而后,又渐渐地与卓刀泉寺结下了深厚的法缘,经常参加法事活动。早在高中时代,他就听说过柏林寺每年举办的生活禅夏令营,心向往之,却怕父母不开心,只得压抑心头的渴望,一直未能成行。
2005年夏天,得知四祖寺将举办第二届禅文化夏令营,他终于按捺不住,成为一名营员,得以见识久仰的净慧长老。两个多月后的“十一”假期,他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短期出家。他兴奋地参加所有的活动,受沙弥戒,跟随老和尚参加老祖寺、芦花庵的奠基仪式,法喜充满。
却没想到,这样的一次机缘,却让他最后完成了心中藏匿已久的心愿,脱却尘世的牵绊,正式踏上追求终极真理和究竟解脱的大道。
多年当学生干部的他,成了四祖寺最活跃的年轻沙弥,他积极参与寺院的各种活动,几乎无处不在。更有幸成为老和尚的侍者,得以亲近老和尚,随侍钵瓶,修学佛法。
八年时间,师徒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无论是历史性的大场面,还是点滴生活细节,都成为崇谛法师最好的活教材。“虽然我学佛的时间比较早,但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那基本上属于盲修瞎炼。直到遇见老和尚,才慢慢真正确立信仰,可以说,老和尚是我的法身父母。”
与“生活禅”水乳交融的深厚法缘
颇富戏剧性的是,少年时期“高调学佛”、“佛里佛气”的他,在真正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成为一名僧人后,反而一直忙于张罗各种似乎与“修行”无关的寺院事务。他语速极快,让人很难跟上他的节奏;他疾行如风,随时应声出现在每个需要的角落。他像孩子那样灿烂鲜活,阳光坦诚,又像长者那样沉稳持重,应付裕如。他个性鲜明,有着同龄人难以企及的世出世间学识和洞见,却又无私无我,像盐巴溶入海水那样,把自己完全“融化”到大众中去。
“这一切,都是受老和尚开创的生活禅、以及他自己完完全全以身作则践行生活禅的影响。”崇谛法师说。
有一个悖论是,一些众人仰望的“大人物”似乎只可远观其光芒,如果近距离接触,会因为发现他们身上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缺陷,“这一点在老和尚身上恰恰相反,贴身侍从八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日益惊叹老和尚不可思议的思想境界、博大胸怀和人格魅力,尤其理解老和尚提出生活禅的良苦用心。”崇谛法师认为,生活禅绝非仅仅是一个修持法门,而是有着“中国第一学问僧”美誉的净慧长老开创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修学体系,它完全融会贯通自己全部的佛学理论见地及功夫,结合自己饱经沧桑的人生历炼和洞察,站在振兴汉传佛教的历史高度,让佛法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水土”及普通大众根机。
总体来说,生活禅就是在禅的智慧觉照下,以清净的生活替代染污的生活。生活在禅的世界里,就是要用大智慧审视生活,用大慈悲普度众生。“千万不要把生活和修行打成两截,不是整天坐在禅凳上打坐才叫修行,或者什么事都不干只管整天念佛才能往生,生活和修行应该完全融为一体,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修行的功夫恰恰就是在生活中去锤炼和应用,在自利利他的事业中去‘转’自己的烦恼习气,在每一个当下觉照自己的念头。”,崇谛法师说,千万不要指望临时抱佛脚,“人生就是一条相续不断的念头的河流,如果不能在生活中炼就对念头的觉照功夫,临终时根本无法面对如生龟裂背一般的四大分离而保持正念。”
这就是崇谛法师为大众服务的根本动力,而生活禅犹如“永动机”。
本以为夏令营结束后,崇谛法师可以有几个小时的完整时间接受专访,却被两次中断。其中一次,是一位从事佛教音乐研究的音乐学院女大学生,带着一盘原创佛乐音碟,向崇谛法师请教。令我们惊喜的事,在一边旁听的我们,见识了崇谛法师罕见的艺术品位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
从融通世出世间学养的老和尚身上,崇谛法师看到了“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范本。“一切学问和法门都能成为度生的方便,儒释道三家共同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脊梁,尤其是儒家思想,对世人影响尤为深远,学习后一定会对弘法很有帮助。”
一位年轻的夏令营义工评价崇谛法师时说:他不仅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简直是一个习惯了疲倦的人。
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崇谛法师是一个超越了疲倦的人。
这一切都是因为——信仰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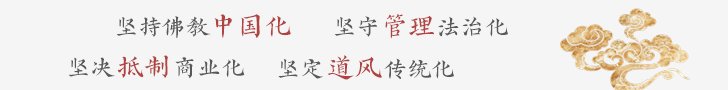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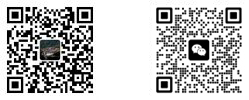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 42112702000026号
鄂公网安备 4211270200002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