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访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做人的佛法》翻译者中嶋隆藏先生
2013年初春时节,身为国际知名学者的中嶋隆藏先生,读到友人赠送的一位中国八旬高僧的著作,心中无比欢喜赞叹,并萌生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要向这位高僧当面请教,而他自己,亦已是一位古稀老人。
中嶋隆藏先生在世界闻名的日本东北大学任教四十余年,是著名的汉学家,研究中国从六朝到北宋儒释道三教关系,目前仍然是东北大学名誉教授。他读到的书籍是净慧长老的“生活禅”系列著作,包括《生活禅钥》《做人的佛法》《守望良心》等。
正当中嶋先生满怀期待地准备到中国湖北黄梅四祖寺拜谒净慧长老时,无常这一铁律突如其来地击碎了这一美好愿望。今年4月20日,长老功圆果满,安详示寂。中嶋先生深深叹息自己与长老“缘悭一面”。
然而,作为一位学贯古今、胸怀世界的大学者,中嶋先生将自己对净慧长老的崇敬与缅怀之情,化作行动的力量。从今年5月开始,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眼花,亲自将《做人的佛法》翻译成日文。
今年11月初,中嶋先生携夫人与好友何燕生教授等一行9人,前往中国湖北,参加第四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行囊中有三本《做人的佛法》日文版样书,还有一篇研究生活禅的学术论文《汉译佛典世界中的布施思想——法苑珠林、嘉兴刻藏捐资者、净慧法师》。
在紧凑的论坛日程表中,中嶋先生十分高兴地抽出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接受笔者专访。中嶋先生交往二十年的好友、日本郡山女子大学教授何燕生先生亲自担任翻译。
净慧长老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
“书是何燕生教授给我的中文版著作,大概是今年二三月间,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完全是耳目一新!”
采访刚开始的时候,为了拉近与笔者的心理距离,中嶋先生努力跟笔者用发音不太标准的中文作自我介绍。“我2006年从东北大学退休了,这一年的秋天到武汉大学讲了半年关于儒释道方面的课,为我做翻译的还是现在四祖寺的当家师崇谛法师呢,他是学日语的,当时在武汉大学读书。”
这位满头银发、慈祥和蔼的老人,衣着十分朴素,脸上始终流溢着温暖的笑意,仿佛一位亲切的邻家大爷。
“我今年71岁了,已经到了孔子的年龄,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是,我眼睛很不好,在电脑前工作一个小时就受不了,所以,《做人的佛法》翻译的进展不快。何燕生教授还催过我,说我太慢了,呵呵。”
谈及触动翻译念头的动机,中嶋先生说,首先是被净慧长老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打动,在历尽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各种磨难之后,长老不仅没有变得消极抱怨,反在年过花甲之年甘为众生做牛马,恢复重光或住持了十余座中国著名的佛教古道场,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僧才队伍,为无数在家男女弟子授三皈五戒。
对于净慧长老倡导的生活禅,中嶋先生认为具有巨大的普世价值:“因为无论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欧美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要生活,净慧长老的生活禅,用现代语言,提供了十分生动实用的生活指南,只要善于运用,就可以让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也让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很和谐,甚至最终获得解脱,直到成佛。”
选择《做人的佛法》进行翻译,中嶋先生是用“世界标准”来衡量:每个国家的人都有学习如何做人的问题,如何做一个既自利,实现自我价值,又利他,将责任和义务落实到位,报效“父母恩”、“国家恩”、“众生恩”、“三宝恩”。正如净慧长老倡导的做人宗旨:“觉悟人生,奉献人生”。
中嶋先生特别赞赏民国年间“人间佛教”倡导者太虚大师一首著名的学佛偈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净慧长老的生活禅著作中多次提及这首偈子,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学习。”
《做人的佛法》是净慧长老为弟子们讲授的两部佛经的合集,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善生经》讲记,下半部分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 报恩品》,内容十分贴近生活,说理透彻,语言生动丰富,旁征博引,诗词典故众多。尽管翻译工作非常辛苦,中嶋先生却没有将本书“直译”一番就“塞给读者”,而是还打算运用自己十分深厚的中国国学功底,结合日本文化和社会实际,做详细的注解,以便日本读者能读懂,甚至喜闻乐见。“这份工作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本书要到2014年上半年才能出版。”
生活禅非常值得日本佛教界借鉴
因为历史和现实种种因缘,日本佛教已经基本成为葬礼佛教,对普通民众的心灵世界和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中嶋先生说,在这一点上,他完全认同株式会社寺院经营企划公司社长薄井秀夫先生的观点(编者注:可详见对薄井秀夫先生的专访)。
中嶋先生讲述了自己母亲去世后的一番心路历程。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嶋先生的心理,以下引述薄井秀夫先生论文中的论述:
日本的寺院,主要是以“檀家”(信徒)为对象从事着各种活动。因为“檀家”是以父传子,子传孙来延续,所以,即使世代改变,与寺院的关系不会发生变化。这使得寺院活动的基础变得如同磐石一般坚固,同时也成为了导致寺院活动停滞不前的原因。檀家以外的人,基本上不能参加寺院的活动。
大多数日本寺院由1~2名僧侣管理经营。而且,大多数僧侣都有家室,因此大多数寺院的住持是世袭制。这意味着寺院业已成为一种家庭式经营机构了。其中,住持的妻子承担着接待檀家(在家信徒)等事务,在寺院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寺院,它们每天的具体活动是些什么呢?
基本上是做功课和杂务。早晚在大殿诵经,打扫寺院等。不过,平常极少有檀家(在家信徒)来寺院,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来。只是因各地的习俗不同,有的地方还有“月拜”的习惯。即在去世不久的逝者的忌日,僧侣前往其家中访问,为死者举行诵经活动。四、五十年前,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活动,但近年来,在城里举办这类佛事活动的寺院越来越少了。
寺院最忙碌的日子,是大多数人休息的周末。周末一般安排为檀家(在家信徒)的祖先举办“年忌”法会。仅仅周末两天时间,有不少寺院甚至要举办10场以上的“年忌”法会。除了办法会、讲经活动外,还要与施主的家人一起举办“追念故人往事”的活动。此外,檀家的家中如果有人去世,住持还有担当葬礼司仪的角色。虽然因寺院的规模大小略有不同,但一般的寺院1年都要举办大约10~30场葬礼。
中嶋先生告诉笔者,因为日本佛教和寺院的现状,让他在去年母亲去世后,没有选择到寺院举办佛教葬礼。“一者是,日本的僧人跟普通人一样结婚、吃肉、喝酒,僧人只是一种职业,我在内心里不相信他们有超度亡者的法力;二者是,在寺院举办佛教葬礼,要交一笔可观的金钱,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中嶋先生认为,日本佛教必须进行大改革,要让佛法从寺院和经书中走出来,活学活用,能够真正解决民众的精神痛苦,让他们生活得快乐和解脱。“在这一点上,净慧法师的生活禅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著名汉学家书柜里几乎全是中文书
在做翻译的间歇,何燕生教授告诉笔者,之所以对净慧长老的生活禅思想如此契合,与中嶋先生中国国学的底蕴十分深厚有关,在这方面,甚至一般的中国人都难以望其项背。“老先生家里没有日文书,几乎全是中文书。”
“其实,在东北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好好研究日本文化的,结果发现日本文化的渊源在中国,因此,我就下决心学习中国文化了,这一过程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中嶋先生笑着说。
中国文化的核心无疑是儒释道,中嶋先生就从这里下手,研究三教之间的关系,异同与融合,时间段为六朝、隋唐、北宋,先后出版了《六朝思想之研究》、《六朝士大夫如何接受佛教思想》、《云笈七笺基础研究》等功力扎实的著作,同时也有《中国的文人像》这样生动可读的著作,甚至还写过一本名为《静坐》的书,分析三教对静坐的理念和方法。此书因为颇受欢迎,在台湾被译成中文出版。
“我是1965年进大学学习的,那个时候学习中文很困难,因为中日还没有正式建交,不能像过去的日本留学生那样,几乎可以随时到中国留学,只好在家里学‘哑巴中文’,所以中文口语不好。”
尽管如此,中嶋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悉程度令笔者既吃惊又惭愧。他像谈论老朋友那样,说到六朝名士阮藉、嵇康,谈及佛教界里程碑式的大师道安、慧远、僧肇,告诉笔者葛洪的《抱朴子》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名作,前半部分写成仙求道之术,后半部分是儒家思想。他还谈到中国佛教界内甚少涉及的六朝末期及隋唐流传甚广的“三阶教”,因为过于偏激,为当局所禁止。在这一过程中,中嶋先生随便说到一些古汉字的多种含义和用法,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却闻所未闻,深感汗颜。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可以说,有机会采访这样的大德,是人生莫大的荣幸。
令笔者惊喜的是,虽然研究领域是中国中古文化,但中嶋先生一点也不“古里古气”,而是对现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同样十分关切,他对鲁迅、巴金很熟悉。
连电视频道也喜欢看中国的。“我很关心中国的教育状况,那天我看中国的电视教育频道,里面说到中国的历史变迁,其中的表述很不准确,主要的问题就是封闭式思维,认为中国历史和文化是自成一体、独立形成的。其实中国的文化一直是与周边国家和外来文化的不断交融中成长起来的,绝非关起门来发展,或者一成不变的。正因为有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文化才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才没有被其他文化征服和消灭。”
谈到这里,中嶋先生完全超越“日本人”的身份,显露出国际学者的博大胸怀:日本人也有这样的认识误区,二战以前,日本人受的教育就是“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如今日本一些著名的右翼分子还是持这样的观点,比如石原慎太郎先生。“其实,日本文化,发展同样是在与周边国家融合产生的,渊源主要来自于中国,日本号称‘大和民族’,‘大和’的意思就是融合。”
笔者不禁感叹,如果大家都有中嶋先生这样的智慧和襟怀,国家之间哪有如此众多造成无数生灵涂炭的战争呢?人类怎么会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从而导致十分严重的生态危机呢?
不知不觉间,一整个上午的采访已经结束,转眼到了午餐时间,可中嶋先生依然精神攫烁,意犹未尽。他亲切地对笔者说,我们还可以闲聊一下,放松放松。
“我爱听西方古典音乐,特别喜欢柴可夫斯基,听了让人很宁静,而贝多芬的音乐起伏太大了,容易让人情绪动荡。”说着说着,中嶋先生突然唱起了中国的西部民谣,“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声音悠扬清亮。出人意料的是,紧接着,他突然唱起了中国的《国歌》。笔者心里愣了一下,心里嘀咕,“这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么?”,但很快也跟着唱起来。当唱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时,中嶋先生突然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敌人就是我们!”然后哈哈大笑。
哈哈哈,笔者与何燕生教授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幽默逗得大笑起来,空气中充满了温暖的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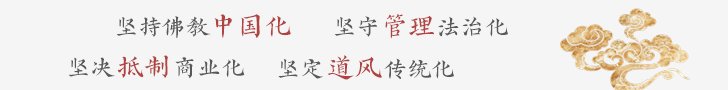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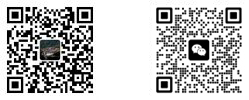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 42112702000026号
鄂公网安备 42112702000026号